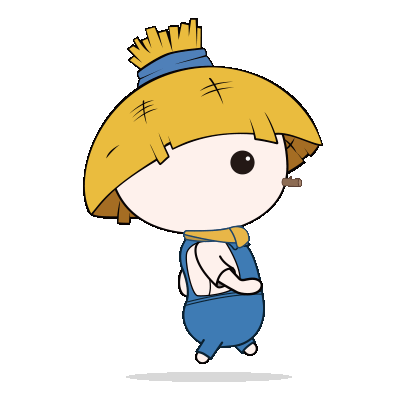“雨濛!”沈棠因想要开口已来不及,只能轻声呵斥,“你不要乱说。”
在这世上,没几个人能镇得住杨小姐,连她身在高位的爹也不行。但沈宗良可以。
小时候她在沈家,因为贪玩,差点把沈老爷子精心养了许久的几株鬼兰从湿沼泽里拔出来,沈棠因在一旁拉都拉不住。
沈宗良只是喝了一声,便叫杨小姐丢开了手,动都不敢动。
杨雨濛闭拢嘴,小心去看沈宗良的脸色。
只见他微垂着眼眸,一身清冷月色,目光全落在那条白色羊绒披肩上,不知在想什么。
过了几秒,他才回头淡淡瞥了杨雨濛一眼,看得她心头一凛,闭上的嘴巴合得更紧了。
沈棠因又问:“小叔,这是钟且惠落下的吗?”
羊绒雪白,不必凑近就能闻见上面的曼妙香氛,也不像她叔叔的东西。
沈宗良没回答,修长的指骨收紧了,眸色渐深。
最终,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
等这股压迫感消失,杨雨濛才急急挽上棠因的手臂,“棠因,你小叔叔那是什么意思?”
沈棠因今天多喝了两杯,疲于应付,“我不知道。但如果你想嫁给他的话,就别在他面前说这些话了,会让他看轻你。”
“嗯,好吧,我知道了。”杨雨濛受教地点头,随即又欸一声,问:“不是,你从哪儿听说我想嫁给他?”
沈棠因被她这副样子弄笑,有时候又觉得雨濛可爱。
她戳了一下杨雨濛脑门,“还用听说吗?你的心思都写在这儿了。”
宴席散场时,已经是凌晨一点多。
出于安全考虑,冯幼圆一定要留且惠在家里住。
她说:“外面这么黑,你那个小区又远,派人送我也不放心的,今天就和我挤挤。”
从读大学起,钟且惠就在外头住,每天走读。
小时候那段抹不去的经历成了永远的伤疤。
钟且惠很怕和人同住,长着青苔的洗手台简直成了她的噩梦。
哪怕后来到了江城读书,水龙头前人多,她也从不去争,宁可多绕几步路去别处。
“这也不能叫挤吧,”钟且惠指了下中间的大床,“睡三个人都有多。”
庄新华从她们当中露出颗头,“不挤的话,那再加我一个吧,我睡中间。”
对视过后,且惠和幼圆同时往他左右两只脚上踩下去,用了十成力道。
房间里传出一声惨叫。
庄新华疼得冒汗,一时不知道该抱起哪只好,只能面目狰狞的,趔趄着往后倒退到沙发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