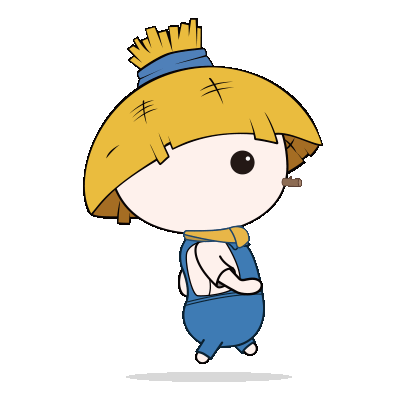三民的爹啐了一口,不屑地说道:“你让她借去,我不是晾她,她借不来,谁家有五百现大洋?进士爷家有,问题赌博的钱他不借,这谁不知道,你看着,怎么去怎么回,比算的都准。”
三民不稳心,要是真借来呢,年已二十的三民已经有了私心,若由着大哥这么作下去,这个家马上就要完蛋,心软的老娘心疼大儿子,难道就不想想小儿子的亲事还没着落呢。
三民恨大哥,恨得牙根疼,恨归恨,但他却毫无办法。
“借不来你还让她去?叫我说就得让他吃一次大亏,不然你这次替他还了,下次呢,下下次呢?”
三民气哼哼地说,心里却埋怨老娘心软,惯孩子也不是这个惯法,他都多大了,二十五了,二十五了还惯,早晚惯出事,这不,出事了吧,五百大洋,你就不想想你的面子那么大。
“这个妻侄羔子,可让他作毁了,要么你把你娘拉回来吧,咱爷俩去看看,不行的话给跟人家磕头,让饶过你哥这一回。”
三民的爹说道,然后叹息了一声,作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他实在想不透,儿子大民咋混蛋成那样,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,他百思不得其解,难道祖坟没埋好?一刹那,他动了迁坟的念头,可是,也就是一刹那的事,迁坟可不是小动静,还是先把眼前的事了了再说吧。
三民跑着追上了哭哭啼啼的老娘,生拉硬拽把她弄回了家,然后跟着老爹往街上奔去,他爷俩怕去晚了大民的手保不住。
路过李家麦场的时候,三民眼馋地看着一帮伙伴正嘿哈的练武,而进士爷的小孙子小安则站在一边不停地指点着。
看到三民爷俩,小安就问:“二大爷,凑够钱了?”
三民的老爹哼了一声,随即摇摇头,无奈地说道:“侄子,二大爷我也不瞒你,就我家,卖了也凑不够啊,俺爷俩去看看,我磕头下跪也行,看能不能让饶过大民这一回,你说咱庄户人家,要是少了一只手,这以后的日子咋过啊,那不是废了么,要饭也不得劲啊。”
小安想了想说道:“要么我跟你们去看看。”
三民的爹一喜,进士爷的大名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他孙子出面,说不定人家能给他一个面子,一念至此,他感激地说道:“那就麻烦侄子了。”
阴平街的赌场真不咋地,就是一个小院子,三间屋,门后一个土炉子,上边坐着一个铁壶,正汩汩往外冒着热气。屋子东边一桌牌九,西边两桌麻将。小安跟随三民爹俩进屋的时候大民被捆了手脚,像个狗一样蜷缩在墙角,而牌九的赌局并没有停止,哗哗洗牌的声响闹腾的正欢。
大民看到老爹,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爹。这一声有委屈,但更多的是希望。缩在墙角的他想了很多很多,但是断掉一一只手的后果无时不在脑中晃悠,那样的话,他觉得生不如死,一只手不单玩不了牌了,要饭吃都费劲,至少一手拿碗一手拿棍吧。
看到来人,坐在牌桌上的人并没有一个招呼,反倒继续玩,庄家还故意地大喝道:“人对,拿钱。”
三民的爹不敢吱声,一分钱没带,没脸吱声,可是他扫了一圈,确定了坐东面西的那个人才是正主,他噗通一声就跪下了,毫无征兆的跪下了。
庄家被吓了一跳,扭头看向三民的爹,然后啐掉嘴里的烟头道:“这谁,干嘛呢,咋不吱声就下跪,啥意思嘛,你们知道么?”
几个打牌的心知肚明,却都摇摇头,意思不知道,装糊涂谁还不会。
“我是他爹。”说着,大民的爹一指大民,“我给诸位庄家磕头了,求您饶了他吧,我家实在是没钱啊,都让这个混账东西输光了哇。”
说着,大民的爹嘭嘭嘭磕了三个响头,实实在在的响头,听得人都觉得疼得慌。
庄家乜斜了一眼大民的爹,摆弄着桌上的牌九道:“没钱?没钱就不要赌,赌场有赌场的规矩,愿赌服输,问题是这小子搞歪门邪道,出老千,坏了规矩就得受到惩罚,没钱没事,那就拿手抵,谁让他发贱的。”
“都老亲世邻的,玩这招,那哪行,还不知他出老千赢了我们多少呢,哪能就这样算了。”
一个赌徒跟着庄家附和道,不用说,是跟大民一起赌的赌友,此刻竟然一句都不替大民说话,可想而知有多恨吧。
“爹,咱走,不求他们。”
三民说道,伸手就去拉老爹,因为大民出老千,老爹跪着求人家,三民觉得这脸丢尽了,传出去能丢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