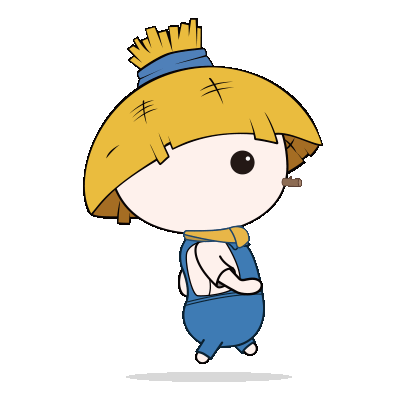徐振英认出那是方家大房的嫡长女,二皇子的未婚妻方如玉。那日在牢里被那几个太监按着打了脚底心的女子。
当时看着已是血肉一片,想必长时间无法行走,两姐妹便一直躲在这驴车之中,甚至就连出恭这样的事情都是在车内解决。
徐振英方才已经体验到方老太那火辣的脾气,果然方老太一听这话就怒了,“我方家簪缨世家,怎养出你这种古板的性子,你祖父都没有你这般迂腐!就她那连自己姑娘都保全不了的窝囊性子,还指望她能养出个举人秀才?我看她那庶子早就被养废了,哪里还指望得上?倒是你,横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,家里的夫子就只教了你倚赖幼稚卑屈于男子?”
帘子后的方大小姐似乎呆愣了几秒,随后微微啜泣了几分,当真是我见犹怜,“祖母为何如此瞧不上我?所谓不问妇礼,惧失容它门,取耻宗族。这些都是您教给孙女的道理,怎的如今总觉我古板迂腐?若真觉得孙女碍了您的眼,孙女一封信去到琼州,请二爷早些来接孙女,也免您见了孙女总是生气。”
“听听,听听,这说的什么话?你如今当真是泥捏的,说不得,碰不得。还有,你如今已是罪臣之女,别再妄想着二殿下会遵守先帝的婚约娶你过门!”
“祖母,二殿下没有写信退亲,证明他心中不介意孙女的家世地位。我与二爷一起长大,他是什么性子,我清楚得很。他必不会学那陈世美负我方家。况且他离京之前孙女也说过要等他回来履行婚约。君子信约守诺,好女不嫁二夫,只要一日不见退婚书,孙女便一日是他周家妇。”
方老太显然被孙女气得不轻,只恨大媳妇那榆木脑袋教出了这么个拧不清的东西,“方家被判流放不足两日,二爷远在琼州,收到消息那也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。他周家人各个薄情寡性疑心深重,你当自己是什么国色天香不成,二爷愿意守着你一个罪臣之女当正妻?”
帘子后面的人一顿,呼吸似急促了两分,虽然语气不重,话里话外却听得出是个极其执拗的人,“那孙女也愿意等着,只要他一日不提退亲,孙女便一直等着。再说,孙女相信二爷,等二爷在琼州站稳脚跟,必定会风风光光的娶我过门。到时候孙女一定不忘尽孝,将祖父祖母爹爹娘亲都接到琼州去享清福。”
“哎哟…”方老太太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,面露深深无奈,“真是冥顽不灵,怎么也说不通……”
方老太太跟孙女斗嘴斗得你来我往,似乎这才看见旁边一直站着的徐振英。
方老太脸上闪过一丝尴尬,低咳两声,有些不自然道:“叫徐六小姐看笑话了。”
徐振英看了一场热闹,心中倒不以为然,方大小姐也才十六七岁,按照现代年龄还应该在读高中。这个年纪最是叛逆认死理,横竖道理都是说不通,只得撞了南墙才晓得回头。
可见方老太一脸灰白之色,似极为着急上火,徐振英也只好压低声音安慰了几句,“老太太不必如此着急,方大小姐整日只在马车里活动,这一寸小天地也局限了她的思维,也总得给她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和念头。姑娘家嘛,多见见人,多看看风景,这去往黔州的路千难万险,等方大小姐见得多了人间疾苦,也许便会觉得儿女情长不过小事。”
方老太哪里不知这些道理,终究是关心则乱,如今听徐振英这样说起,心头越发无奈,只得点头生受,“但愿如此。你也看出来了,我那孙女是个执拗不知变通的,我只怕她多走了弯路。”
“方大小姐年纪小,又一直养在闺中,此番磨难必定让她开阔眼界涅盘新生。方老太太不必太过着急,省得先气坏了自己身子。”
方老太太听着这一句一句的,只觉得徐振英分外懂事又贴心,终于露出些许笑颜,“你这小丫头,嘴也忒甜。改日见见你爹娘,我倒要问问怎么教出你这样懂事乖巧的姑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