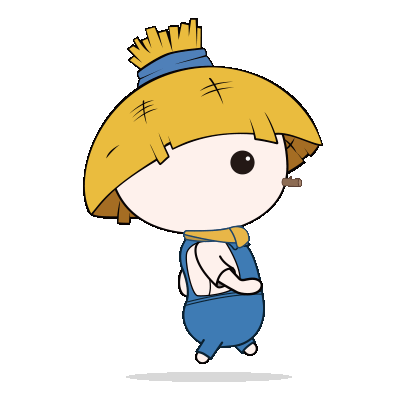挞懒哼了一声道:“刚开始之时,我也是这么想来着,可如今看来,怕莎宁哥不是为了什么隐情,而是为了她心底的私情了。”
大迪乌笑着说:“看来你认定了那臭娘们儿与杯鲁兄弟有私情了。不过,这也难说得很。”
挞懒气愤愤地说:“本来斡离不那边一得到了消息,立马就派人混进了燕京,准备接应于她。刚开始还能有些消息传递出来,可后来呢?斡离不派去的线人竟然全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那臭婊子向来心狠手辣,那些线人已经被她下手除掉,那是决然无疑的了。”
大迪乌道:“把别人全都除掉了,这寻找到杯鲁的功劳吗,在皇上跟前那可就得全都算到她一个人的头上了。”
挞懒道:“你总觉得那臭婊子全然是为了功劳,我猜她为了功劳只是其一,俘获杯鲁兄弟的心,把她自己变作杯鲁兄弟的老婆才是她最想要的结果。把其他的线人逐开或是除掉,最方便的是她好与杯鲁卿卿我我地培养感情。
你想想,寻找到杯鲁兄弟的功劳虽大,可她能得到的不过是些更大的官位与金银,以及为她的父兄多争取到些加官进爵的机会。可是她如果变成了杯鲁的老婆,那她下半辈子可就有了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
况且杯鲁兄弟英俊倜傥,在咱女真人的年轻一辈中,人才最是出众难得。莎宁哥那娘们儿对杯鲁或许是动了真情,也都说不定呢。”
大迪乌道:“你还别说,莎宁哥那娘们儿也真是个人才,也不知她到底是修炼的什么功夫,都三十好几的人了,而且还嫁过了人,愣是驻颜有术,保养得宜,看上去竟跟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一般。”
挞懒哈哈大笑道:“据刚开始派去燕京的线人回报所说,莎宁哥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,在杯鲁兄弟面前温顺的像只猫儿一般,一声老爷叫出口来,都能把男人的骨头给叫酥了呢。”
张梦阳心想:“这个莎宁哥,原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,为什么她叫那个杯鲁,也是叫做老爷的,倒像是和暖儿商量好了似的。可是被叫做老爷,真不如被叫一声公子或是少爷的,更能令人觉得心醉。听他们的话里,那杯鲁与莎宁哥是躲在燕京城里的,只不知他们躲在了何处,与我和暖儿居住的地方有多远。”
大迪乌笑道:“南朝妇人对自家男人多是以相公、官人、夫君等称之,她既不伦不类地把杯鲁称作是老爷,那自是以婢妾自居了。”
“哼,她倒还有自知之明,知道杯鲁的正室夫人乃是多保真公主,就算使尽手段把杯鲁给笼络住了,如愿地嫁给了他,其身份也只能屈居在公主之下。想来她的内心里,那一声声的老爷叫出口来,也总不会十分地心甘情愿吧。”
大迪乌叹道:“杯鲁兄弟失踪的这些时日里,听说多保真公主时常地跑到宫里缠着皇上哭闹。皇上这次亲临大军布置攻打居庸关,也有着些躲避公主纠缠的因素。虽说那莎宁哥有些私心,但也愿她终能保得杯鲁兄弟无恙,使得他与多保真公主这对少年夫妻早日团聚才好。”
张梦阳心想:“这个杯鲁之所以年纪轻轻的便大受金国皇帝的宠信,原来他竟是金国公主的丈夫,皇帝的女婿,难怪那个名叫莎宁哥的女人要竭尽心力地讨好他呢。
能把一个公主娶到手里当老婆,那得是几世修行才能得来的缘分哪。我姓张的要能有这样的福气就好了。”突然又一想:“不对,就算他娶到了公主就一定跟稀罕么?萝卜白菜各有所爱,在我张梦阳的心里,他那公主可未必及得上我心里的郡主呢。”
一想到小郡主,心中顿时伤感起来,也不知道自己被这两个家伙捉在此间,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。想到刚听韩打虎所说的小郡主趁着自己昏迷与那毡帐里没人,曾在自己的脸颊上印了一吻,心中顿感甜蜜,眼下所受的屈辱,似也在一时间被冲淡了许多。
接下来还听他们说了不少话,有军情有政情,拉里拉杂地说了许多,他一直都沉醉在小郡主于自己脸颊上的那一吻中,对他们后来到底都又说了些什么,竟是全未入心。
身旁的韩打虎与高保奴也是趴伏在那里一动不动,连呼吸间都显得是那么的小心翼翼。